|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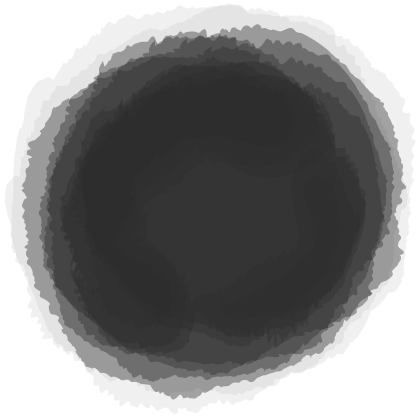 
在这里的银艺师他们都是传统的手工制作,每件工艺品都并不花哨,从外观到修饰艺术的雕刻都是当地民俗的图腾,蕴含着整个月亮山区苗族的文化。了不起的匠人,我们来认识月亮山下最后 的银艺师——老李
银饰原料——银条
银饰是月亮山地区苗族姑娘不可或缺的妆饰品,在生活中占有重要的意义,是财富地位的象征。女人在月亮山区的苗寨里地位极高,从出生到嫁为人妇的这段时间里,家里除了生活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为女儿准备银饰上,在生活困难的50、60年代,他们往往会以家里最值钱的劳动工具——耕牛着为筹码,到别的地方去兑换白银,为女儿量身打造银饰。 月亮山区一套完整的苗族银饰
银饰在这里的苗族生活里无处不在,逢年过节或者婚嫁活动,银饰从来都是主角,没有银饰你是没有脸面去参加的,甚至踩歌堂的队伍都是根据银饰的多少而排列。一般她们会有两套以上的银饰,一套是童年时期表演性用,一套着为嫁妆,嫁妆银饰会随着女儿“嫁”到男方并保存下来,它将伴随女主人的一生。
银饰的盛行衍生了许多银艺师,在银饰盛行的年代里他们以此为生,以至于有很多外县的银艺师都会跑到这些地方来卖手艺讨生活。然而,信息时代的到来,80、90后的人们已经逐渐汉化,不断追逐潮流感,加上高效率、低成本的机械生化生产使这个行业雪上加霜 ,生存空间十分严峻,同时也导致无人愿意传承这门手艺。
现今,月亮山区从江境内仅有8人还在从事银艺师的行业,其中6人还属于他乡的流窜师傅,与当地姑娘通婚而被同化的1人,土生土长的师傅仅仅1人。银艺师正走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上,坚持或者放弃全由市场决定。
走进银艺师的生活,仿佛穿越到了70、80年代。银艺师的工作坊往往都是最简单、最不起眼的“棚户”,工作坊里摆放的都是最原始的银器制作工具,各种刻凿、各种模具多达一百多件,杂而不乱。
老李是外地流窜到月亮山区并和当地苗姑娘结婚而定居下来的银艺师,今年60岁,通过访谈得知,他是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的人,20岁出头的时候来这边打银为生的,到现在在这边生活已经40年了,从加勉乡的真由村、加鸠乡的上半乡、到光辉乡的加瓦村、加页村的大部分银饰品均出自老李之手。
在访谈里,笔者在打听他收徒的情况,老李直摇头说,40年的卖艺生活里,从来没有人主动想跟他学习过,主要是这行的工艺比较繁杂,收益并不高,基本维持生计已经很不错了。在工艺传承上老人显得十分无助,在这里50岁以下已经没有人再会打银饰这门手艺了,就连他儿子都没肯跟他学,事实上他也不想让孩子学这门手艺,希望孩子能够考上公务员。
这边的苗族银饰复杂而且非常沉重,完整的一套轻则十多斤,重则二三十斤,老李现在依旧每天坚持他银艺师的生活,原来能够十天左右完成一套,现在要多花上一半以上的时间。
月亮山区的苗族银饰都是真金白银,图腾样式世世代代从未改变过,苗族同胞在坚持着自己的文化,银艺师也在坚持着自己的工艺文化。在原来挨饿的社会里卖艺可以求生,而现在连传承都看不到希望,传统工艺的传承将何去何从?
社会在进步,传统工艺也在发生很大的改变,机械化的生产不仅效率高,成本低,而且工艺更加精美。但是机械并不是万能的,在各路“砖家”的影响下,什么文化的融合,传统与现代工艺的结合等等,统统扰乱了传统工艺文化的传承,很多地方的银饰失去了自身的特色,取而代之的是毫无差异、没有了地域特色、让人分不清了是苗族、壮族还是侗族的银饰。
文化差异在“现代化”进程的浪潮里已经弱不禁风,好在生活在月亮山原始森林下的苗族同胞还没有受到过多的侵蚀,好在传统村落保护和民间传承人保护政策的及时落实,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丝希望,但愿月亮山下最后的八位银艺师只是暂时的孤单。
作者:莫晓树
| 




